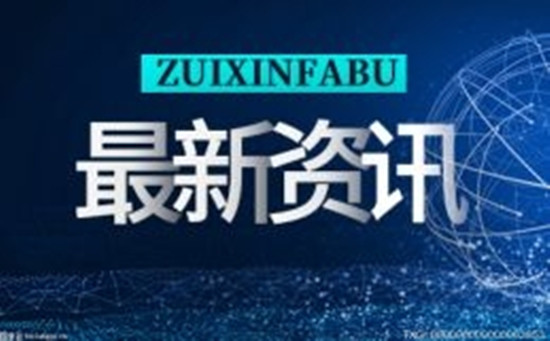我经常与人提到《大明王朝1566》。
相比于《天道》《青瓷》等商战剧突出“商人”的个人魅力,《大明王朝1566》则把“商人”放在了社会大背景之中,能读出更多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原罪
在我们这块以“农”立国的土地上,商人的社会评价,历来低下。儒家认为小人言利,商人会败坏社会风气。法家认为商人缺乏安土重迁的秩序感,不便管理。所谓“儒表法里”,而“商人”这个群体,表里之间,都不是好人。
这其中,朱元璋是最恨商人的皇帝之一。史载:
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,言之颇悉。上曰:“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、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,剥民取利,海内苦之;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,小人竞进,天下骚然。此可为戒。”于是言者愧悚,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。——《明实录》
上古,好闲无功造祸害民者少。为何?盖谓九州之田,皆系于官,法井以给民,民既验丁以授田,农无旷夫矣,所以造食者多,闲食者少。……士农工技,各知稼穑之艰难,所以农尽力于畎亩,士为政以仁,技艺专业,无敢妄谬。维时商出于农,贾于农隙之时。此先王之教精,则野无旷夫矣。——《大诰续编》
把这两段话翻译一下,就是大明遇到了财政困难,烟火不振,大臣们建议繁荣一下经济,但被朱元璋一通驳斥,大臣们被吓得都不敢说话了。
特别要注意朱元璋看不上商人的原因:上古时代的井田制,百姓都老实待在地头劳动,所以“农无旷夫,造食者多,好闲无功者少”。先树一个道德高标——“踏实种地最光荣,投机取巧很可耻。”
“维时商出于农,贾于农隙之时”,这句话更露骨,意思是,压根不许商人成为一个专业群体,只能在“农隙之时”出来活动一下。
至于财政问题,朱元璋是怎么解决的呢?屡兴大狱,以至“檄赃所寄借偏天下,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。”一通抄家,罚没银两无算。
当然,这里得插一句,虽然看朱元璋嘴上把“农”说得如此之好,但生活在朱元璋手底下的“农”们,其实过得也不安逸。如上文提到:“九州之田,皆系于官”,“农”不过就是劳动力而已。朱元璋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:24个儿子,全被封为亲王,赐田40万亩。亲王的后代,从摇篮到坟墓,出生发补助、公费医疗、专家上门、婚丧嫁娶都可以报销、死了还有丧葬费,没处花钱,还月月领俸禄,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:
“我朝亲亲之恩,可谓无所不用,其厚远过前代矣”。“王府将军、中尉动以万计,假令复数十年,虽损内府之积贮,竭天下之全税,而奚足以赡乎?”——《明实录》
简单说,这么一大摊子裙带,吃空了全天下的税负,待遇“空前”。
为了让“农”老老实实种地交税,朱元璋规定,抗税者杀。你说我交不起税,去要饭吧,那也不行。因为朱元璋禁止农民聚众、迁徙,想出村走个亲戚,都要经过官绅审批。想外逃避税,那更是门都没有。
如今很多通俗历史小说把朱元璋塑造得爱人如子、勤政为民,但据《明太祖实录》与《国榷》等书记载“自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八年,各地农民起义百次以上”。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六年的全国人口统计,大明王朝的人口非但没有上升,反而出现了下降。历朝历代中,在建国初期就一度出现人口萎缩现象的,朱元璋虽不是唯一,也足够凤毛麟角。
有种传统说法——“重农抑商”。如果你看字面意思去理解,总以为“农”有多高的地位。其实,朱元璋早就把话说明白了:
“受田之日,验能准业,各有成效,法不许诳”“技艺专业,无敢妄谬”——《大诰续编》
重“农”是因为“农”便于管理——“无敢妄谬”,而非真觉得“农”有多么的淳朴高尚。朱元璋骂“农“,其实比骂“商”骂得更直白,在《大诰》序言中就直接说,天下老百姓,冥顽不化,不严刑峻法地敲打着老百姓,这帮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王法。朱元璋还通过户部晓谕两浙、江西百姓,亲自指出:
“为吾民者当知其分,田赋力役出于供上者,乃其分也。能安其分者,则为忠孝仁义之民……否则,不但国法不容,天道也不容矣。”
马基雅维利在《君主论》中提出:“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,更为安全”“最危险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”,所以要让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敌视,分散社会力量,避免任何一个群体的力量壮大。
这些玩意,在西方轰动一时,但其实都是朱元璋在一百多年前就玩剩下的。所谓“原罪”,本质是权力需要哪一个群体有罪,那么这个群体就有了罪。这是千古帝王的驭民之术而已,并非意味着某一个群体就真的天生无良。别说什么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益,就有人铤而走险。没错,这个世界是有“烂人”,但请想一想用甲拌磷种的大葱、安磷酸泡出来的豇豆……这个世界“烂”的是一些人的欲望,而非特定群体。
穿绸缎的人
明白了所谓“原罪”,你才好理解“商”与“农”之间的真实历史互动。
从来,老实巴交的“农”,名义上都被抬得很高,而“商”被贬得很低。朱元璋立过一条规矩,“农”可以穿绸缎,“商”只能穿布衣。但允许穿绸缎的“农”从来也穿不起绸缎,而被禁止穿绸缎的“商”倒经常有绸缎可穿。
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就有这么一段。商人沈一石穿着绸缎,面见海瑞。海瑞当时就怒了,你个商人,敢犯我《大明律》?沈一石回话,因纳贡突出,皇帝赏的。海瑞开始还不信,认为皇帝怎么可能自己破坏《大明律》,然而事后一查,还真是皇帝亲批的。
沈一石这个角色,是导演虚构的。有人认为,人物原型是被朱元璋亲自杀掉的江南首富沈万三。但沈万三到底是元末明初的人,还是元末就已去世,历史界一直有争议。不过,我想说的是,这些历史细节不重要,重要的是,历史的内核是真实的——大明王朝就是有一些商人得到了极高的官方认可。
就像《绣春刀》中魏忠贤对小捕快说:“你以为皇帝是要我吗?皇帝是要钱。”
“农”也好,“商”也罢,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帮着皇家挣钱,那你就是皇家的好朋友。朱元璋不让商人穿绸缎,但“商”还是穿了。朱元璋不让内臣参与朝政,但明朝的权阉一个接一个。
只要能帮着皇家解决了府库之需,祖训又算啥。当皇帝御批某个商人可以穿绸缎的时候,皇帝会提“立农为本”“重农抑商”这茬吗?不会的。
大明是一个特别有矛盾的朝代。你看宋朝的司马光、王安石,无论他们之间的政见存在何种分歧,但自我道德约束是一致的,士人不经商。而到了明代,大明的权阉都经商,东林党这帮清流也经商。
朱元璋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,是骂“商”骂得最狠的。可嘴上很高调,身体很诚实。在商人连穿衣自由都没有的时代,大明王朝恰恰就是最全民经商的时代。张居正骂严嵩盈利谋私,但张居正上台后,自己家人也参与盈利谋私。
张居正会说自己或自己家人有“原罪“吗?皇帝会因为张居正家人参与商业活动就“抑”掉张居正吗?都不会。政敌经商,是原罪。自己经商,挣得就是干净钱。大明王朝是理解“商人原罪”的最佳样本,充分展示了“原罪”不过就是挑动不同群体之间彼此敌视的舆情手段而已。
当然,这里提醒一句,不要又习惯性地滑入无商不奸的思维。“农”穿不起绸缎,最大原因是明代的账面税负虽不算高,但各种杂七杂八的税累加起来则要命。
宋时亩税一斗;元有天下,令田税无过亩三升,吴民大乐业。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,按其私租籍征之,亩至八斗,而民始困。盖吴中之民,莫乐于元,莫困于明,非治有升降,田赋轻重使然也。——晚明史学家谈迁
败家
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,沈一石自杀了。
出事之前,沈一石可算是个为国分忧的好人。对于普通人而言,沈一石有织坊诺干、织机千架、布庄百家,解决了数万就业;对于大明王朝而言,沈一石向各部门捐资捐贡的数量,载以车计,同时还能出口创汇。更重要的是,沈一石就像地下财政。地方官想办点事,不管公事私事,沈一石都是最好的筹资对象。
这时候,人就容易“飘”,比方说冒出一句:“我们辛苦赚的钱,不偷不抢,我们爱向哪投就向哪投”。
好吧,你的钱?话不落地,马上就让你明白,官家“捧得起你,也踩得倒你”。
历史上的严嵩父子,可不是写写青辞拍拍马屁就能得宠的。史料记载,嘉靖喜欢给群臣出题,一时兴起就抛出一句话,让群臣回答这句话出自哪里,如何解释。连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都回答不上来的题,严世蕃略作思考就能答对。徐阶一向看不去严嵩,但即便严嵩下台了,徐阶还是承认严世蕃的最强大脑,更不要严家父子给嘉靖搞来那么多少钱。
即便如此,嘉靖想拿下严家父子,立马就抄家没产。文臣群体,尚且这般,更何况本就是名义上的抑制对象——“商”。
沈一石,这个被塑造的城府极深的角色,剧中并未说什么出格的话,可改道为桑的政策出了问题,需要背锅侠,沈一石就得死。
不需要有人背锅的时候,连杨金水、吕芳等通天的人都对沈一石客气几句。浙江知府那更是与其称兄道弟。
可需要背锅侠的时候,浙江知府对沈一石,一点也不客气。这样的桥段,历史上反反复复,不乏其例。如很多商人都推崇的胡雪岩。风光的时候,胡是各路官员的座上宾。上海地方官缺钱就找胡雪岩要,什么时候还钱嘛,不一定,但肯定能在政策许可的前提下,给胡雪岩各种优惠政策。可有一年,胡雪岩倒台的前夜,因生丝大战,胡雪岩资金链紧张,却又遇到上海官来要钱。胡雪岩一时为难,说能不能缓一缓。上海官开始还笑着说,是不是担心我们不还钱,没事,我可以给你块地,也可以免你的税。胡雪岩这次是真没钱,还是请上海官理解理解。这下,上海官生气了,理解你个屁,小小的奸商,给脸不要是吧,查他,我就不信查不出问题。资金链紧张,又遇到官方立案查封,胡雪岩帝国没几天就崩溃了,留下一句“勿近白虎”。对于“白虎”这个词,后世很多人简单地解释为“财富”,说胡雪岩劝家人别再经商。但在我看来,“白虎”指的是政商关系,远之生怨,近之则险。
这时候,千万不要说“我解决了多少就业,纳了多少税”。这东西就是双刃剑。没事的时候,这是军功章的业绩。出事的时候,这是“你怎么可能没钱”的怀疑。
对于想整胡雪岩的上海官,胡手底下那么多的产业,就挪不出点钱来?绝不可能,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对于吃瓜群众,胡手底下那么多的产业,还拖欠我们工资,肯定是吃喝嫖赌。胡雪岩被整,手底下的员工,还有人蛮高兴地看热闹。就像袁崇焕被杀的时候,长街十里,吃瓜群众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。人心就是这么无常。
这时候,再去回想浙江知府拍着胸脯地向沈一石说:“咱们都是自家兄弟”。
多讽刺。
我一直觉得。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导演,肯定是正史野史,都看了很多。
比如,沈一石死是死了,但他留下几个大箱子,记录了全部私下交易。这种故事,野史中有很多。像沈一石这样把私下交易都记个账的,将来一旦事发,大家玉石俱焚。还有向藏酒下药的,就等哪天被没收了,看你们谁敢喝。这样的野史故事,特别多。
再比如,《大明王朝1566》刚开始,大家都认为沈一石已经大到不能倒,毕竟五万匹出口任务在那摆着。但事实证明,沈一石说倒也就倒了。而沈一石死了,立刻有人另一个“商”接手。历史上,大清国也一度依赖胡雪岩的庞大商业机器。但能做白手套的人,倒了胡雪岩,还有盛宣怀。甚至同为“商”,盛宣怀与胡雪岩之间不但没有阶级弟兄之情,反而巴不得对方早死。大清朝需要银子吗?当然需要,但成功不必只在你胡雪岩,还可用盛宣怀。
我们经常会沉浸在一种“百折不挠,虽屡经坎坷,依然昂扬向上”式的奋斗观。对于个体而言,这种积极的态度,当然是对的。但对于群体而言,这又有些悲哀,很可能恰恰是韭菜们的人生态度太积极了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所以野火对于韭菜们一点都不珍惜,于是,一代一代的沈一石死去,一代一代的沈一石2.0再把悲剧重演一遍,然后进入沈一石3.0……